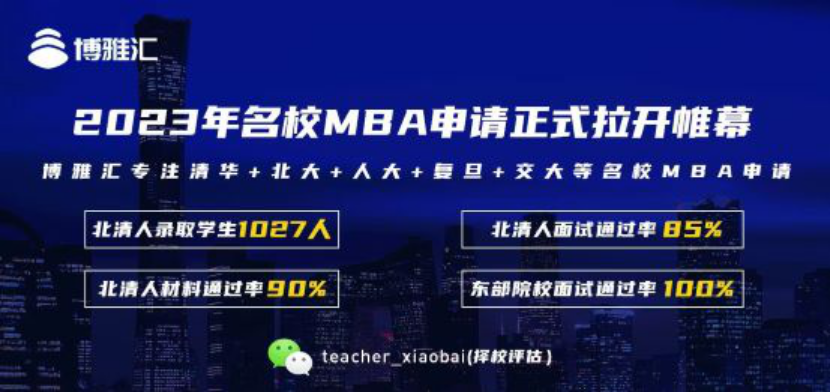复旦商业知识 .
“复旦商业知识”洞悉商业世界,还原实践于管理逻辑中。发掘中国企业管理前沿的研究成果,分享中国企业家管理哲学和最佳实践。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当彭博社记者问到未来一年,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措施让国际社会确信中国是要致力于推进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时,李克强总理回答今年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不断推出扩大开放的措施。并与很多国家提议,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者进行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将中国打造成开放的高地、投资的热土,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关起门来以邻为壑,解决不了问题。
千年之前,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
千年之后,新丝绸之路正在推进,将会给沿线国家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福利改善效果。
本文选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联合出品的《管理视野》杂志(杂志订阅请至文末获取相关信息)。本文作者秦凌为FBK特约撰稿人。
一部以东方视角解读丝绸之路的著作风靡世界,《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荣登英国、美国、印度各大历史类作品畅销榜榜首,同时席卷了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波兰、土耳其、韩国等20多个国家,《开放杂志》将本书描述为“雄伟壮丽,智慧无比”,《商业标准》称赞其为“魅力超凡的世界史”。
这种火爆的情形出现自有其原因。
正如本书作者、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认为的那样,大多数西方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接受一部内容沉闷的文明史”,即以西方为主体的历史叙事:古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启蒙的政治民主带来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思想的碰撞反过来推动了美国的出现,这样一种“西方政治成功、文化优势和道德胜利的颂歌”因为西方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的不断强化,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
在这种“共识”背景下,上述传承脉络之外的国度和文明多少是被忽视或误读的,比如与希腊发生战争的波斯是专制的、野蛮的,把拜占庭变成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土耳其是落后的、奴性的,直到当代的一系列所谓“失败国家”和“没落国家”,这些在西方文明覆盖之外的区域似乎都是“倒行逆施、昏暗闭塞的蛮荒之国”。一直以来,西方总是扮演着发现者、探索者、征服者的角色,在观察、研究他者,即非西方的国度和文明。事实上,“他者”的概念在每一个文明中都存在。
当世界愈来愈趋于全球化的时候,很多西方学者也曾试图破除从自我认知的局限。1998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一部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曾享誉多个文化圈,他在书中把全球社会分成三个集团:以基督教为文化基础的西方(欧美),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中东,和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东亚。并且认为,世界的未来,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儒家三个文化集团的冲突和对抗,尤其是在“血腥的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这一观点似乎被随后发生的“9·11”事件、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危机等穆斯林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地区性冲突,以及西方直接或间接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所佐证。虽然亨廷顿否认了传统的以西方文明构建普世价值,并且正视非西方文化的复兴,但却并没有脱离“自我”的叙事。
基于对这一系列传统认知的反动,彼得·弗兰科潘写就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主张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历史,从中了解他们(西方读者)所知甚少或是完全不了解的某些地区、历史、种族和文化。作者以丝绸之路这一多文明间的通道作为切入点,透视诸文明的接触与演进,从而避开了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偏颇。他说:“事实上,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是文明的交叉点。这些国家绝非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在西方的传统认知中,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勃兴之后独有的现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丝绸之路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了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货物流通成为可能,同样还有穿越亚洲之脊的、连接城镇和绿洲的陆上通道”;而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贸易的商道,政治、经济、文化、疾病甚至是政治制度都在不同民族的穿行与交流中相互影响,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到撒哈拉沙漠以南,从不列颠岛到太平洋东岸,全球化一直在提供着机遇,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视野中,对于丝绸之路以及由其串联和传播的文明,也确实曾经有过更为全球化、更为开放的视野。
北魏时期的《洛阳伽蓝记》就记载过西方诸国来洛阳贸易和定居的繁盛情况。到了唐代,波斯和阿拉伯商人(“蕃客”、“胡商”)是慧眼识珠的鉴宝专家、“波斯邸”是民间性质的金融和信用机构,在唐人传奇和唐代文献中对商胡贩客的描写也屡见不鲜。
在佛教典籍文献中,从魏晋到唐代一直存在的所谓 “四天子”(东方人主、南方象主,西方宝主、北方马主)观念中的“宝主”指的就是大秦(罗马)或者波斯、大食(阿拉伯)和拂菻(指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值得一提的是,彼得·弗兰科潘本人也是牛津大学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这个“宝主”的概念,以及对“宝主”国度“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域沙门迦留陀伽译《佛说十二游经》)、“重财贿……务货殖之利”(玄奘《大唐西域记》序论)的描述,其实可以说是丝绸之路东部古代人群对宏观意义上的西方的集体想象的产物。
确实,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丝绸、黄金、香料、毛皮、马匹等物品的东西方经济贸易通道,它其实还负载了更为广博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文化交流、宗教传播、殖民扩张、霸权争夺等。在丝绸之路上,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曾经或是至今还在影响世界的宗教信仰此起彼伏,不同的族群、城邦、国度和文明萌生、兴盛和湮灭,而丝绸之路的大放异彩,则既是属于沿途众多民族,更是属于世界的。
正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学教授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简史》中指出的那样,“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都由同一套规则管辖,让所有人类都成了‘我们’(至少有这个可能),‘他们’也就不复存在。这三种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赫拉利指出商人、征服者和各教先知是最早跳出“我们”和“他们”这种二元区分的人。所谓的“全球秩序”能否破除“我们”和“他们”之间天然的地理阻隔和文明差异,我们不得而知,但或许重新观览丝绸之路可以为身处十字路口的西方世界提供与多文明对话的路径。
回到本书的宗旨,如果将本书理解为以世界史的视角讲清“一带一路”背后的历史逻辑并没有不当,但在宣传中,将这个历史逻辑简化为所谓的“两千年来,丝绸之路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谁能赢得丝绸之路,谁就能在未来领先一步”,其实多少有一些过于功利和肤浅的误读和曲解。在笔者看来,彼得·弗兰科潘写作本书的立意并不是进行这种智库式的诠释,而是对长时段历史进行更深层次和更多元视野的探索,而作为读者,固然不妨把本书当作“关心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必读书”,但如果从“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角度,如果在阅读的时候超越文化“河西河东论”和“国族轮流坐庄”的迷思而有更深刻的思考和感悟,或许才庶几不负彼得·弗兰科潘的这部煌煌巨著。
本文源引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作者秦凌,文章原标题“丝绸之路上的“我们”和“他们””